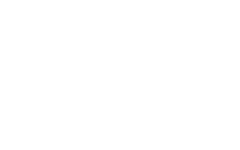- 2025-07-12
- 浏览量:1223
编者按:
宏润博源2025届任同学如愿获得波士顿大学的ED录取通知书。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是美国一所位于麻萨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波士顿大学历史悠久,是美国大学协会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长期以来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居于前五十位,世界排名百强。

从青涩新生到社团领袖,从独行侠到自我和解的探索者,她的成长不必刻意雕琢,只需以真诚为舟,以热爱为桨。那些喂猫的黄昏、改文书的深夜、与石像对望的午后,皆是时光罐中熠熠生辉的沙砾。三年时光凝练成一座“抱着罐子的少女”雕像,静默而永恒,质朴却深邃。这不仅是告别母校的纪念册,更是一篇写给未来的启示录。愿每位读者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倒影:正如少女石像怀抱的陶罐,盛满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真实生长的力量。
——上海宏润博源学校 升学部

三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转来这所高中后第一天的情形。我穿着崭新的、左胸印着校徽的棉袄,有点新奇又很珍惜,因为转来之前的学校并没有校服规定。在那个夜晚我沿着大淀湖的边缘向里走,脚下的草是鲜嫩的绿色,被路灯照得很柔和。步入校园最深处,我看见了一座沉寂的喷水池,上面有尊少女石像,抱罐俯身,裙褶曲折。道路的右侧是一排奶白色的小矮房。我走过去,鼻尖凑到门玻璃上,借着微弱的亮光,和里面的小猫对上了视线。

没过几天,我就从班主任那里得知那排小屋子是几名高年级学生用来安置校园内的流浪猫咪们的地方。在她的牵线搭桥下,我懵懵懂懂地加入了这个尚未成型但充满爱心和热情的“管理局”,也是后来人数众多的校园猫咪救助组织“毛毛乐园”的雏形。我们几个在晚自习结束后结伴顺着湖走进那一间间白屋,给小猫们添水、喂粮、铲屎;在周五放学后相约留校给猫房做大扫除,铆足了劲把它们卧的软垫拍得灰尘乱飞,又横跨整个校园去取拖把和水桶。我还记得早春里累出了一身汗,终于用发酸的胳膊换来了一块略微干净些了的垫子。
“给它晒一晒吧!”远处有人说。所以我把它捋平了,铺到喷水池的边缘上。
我叉着腰休息,看它在石头上躺着、晾着太阳。周围郁郁葱葱。往上一瞥,少女石像朝着我的方向,头低低的。那是我第一次对这里生出归属感。
可能是清晨,又或许在日中,我蹲着同猫平视,抱罐少女像在我们周围投下长短不一的剪影。在照顾猫咪们的过程中,我逐渐学会承担责任,这种勇气帮助了我迈出更多第一步——我加入了社团;我登上舞台,和几个不熟的同学搭档唱歌;我加入了学生会;我生平第一次做活动主持人;我用几周的时间磕磕绊绊地写下了我的第一篇学术大论文;我在假期受邀到学校当学生助教;我的画挂到了艺术展最中心的位置;我成为了一个社团的社长;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创办了一本令我们自豪的文学杂志。流水一样肆意又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我结识了更多良师与益友,越来越深入和体验这个社区,感受它的温暖,同它一起成长。
一次新学期毛毛乐园招新结束后,我和另外一名园长漫步到如今不再有猫的猫房。夕阳将石像的罐子坍缩成地上一滩水渍似的深灰。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青涩的自己打翻水盆的慌乱——原来那个小团队早从六个人与三只猫的秘密基地,变成了规规整整分出数个部门,有执勤表、会议记录的正规军。猫已经不住在猫房里了。它们的数量翻了几番,没人忍心在这样的夏末用玻璃门拦住它们奔跑撒欢的脚步。
 不知不觉间,我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一名领导者。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感到一点惶恐。毕竟,就像我从前喜欢的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少年维持着烦恼”—这是我前几年的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好像无论逃至何处,烦恼也如影随形:
不知不觉间,我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一名领导者。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感到一点惶恐。毕竟,就像我从前喜欢的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少年维持着烦恼”—这是我前几年的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好像无论逃至何处,烦恼也如影随形:
小学阶段我当了五年事事顺心的孩子王,因此升入初中后在数学上获得的挫折和落差使我一度厌学。我自诩较同龄人更成熟,然而照样逃不过每天积极关注新球鞋的讯息,合适的就盘算着这次又怎么能叫妈妈“拿下”。或者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女孩子想变得成熟因此催促自己学习其实并无兴趣的彩妆,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发誓要减下肥来。高中有段时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缺少社交”,便用笑闹和时间换取了小团体的入场券。随后是再正常不过的流程,一拨人一同吃饭进出玩乐追逐。可泡在这样的友情里一段时间后,我产生了对于从众的怀疑与自我否定情绪。因此我做了些改变,也是测试。
 文学老师赏识我,有一次他问, "but why you're always a loner?(但你为什么总是个独行侠呢?)"
文学老师赏识我,有一次他问, "but why you're always a loner?(但你为什么总是个独行侠呢?)"
“因为这样我才能很自在,很快乐。”
我没有半点蒙骗他的意思。我确实从独行的校园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充盈和自由。我可以不用在听歌时怕遗漏他人的话而去将音量调得很低,不需要为一个不好笑的笑话做出捧腹的样子;我有时间画画发呆听音乐,哪怕挑一个大家都在活动的时间跑到猫房边看看石塑少女以及她沉默的罐子,也是颇有意趣的。我去那里去得越发勤,瞧那座像,放空自己,时而又会想:她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的?又会存在多久?也许我的三年不过是她罐中时光的一粒沙......不过,这已足够让我在沙上建起乐园了。
上文枚举的种种少年维特之烦恼如今看来都显得幼稚可爱:我做不到保持自律节食,那就不要再三发誓减肥就好了。不喜欢化妆,不妨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对维持浅淡友谊感到疲惫,那就尝试一个人。“维持”本身就是最累的烦恼。当我松开手,反而释放了真实的自己。难道所有人都得一种活法吗?
 关于我的申请季:
关于我的申请季:
为什么ED阶段选择BU?
因为我喜欢波士顿。我算是个比较感性的人吧,比起学术氛围更在乎周围环境,所以我不会选一个排名高,但是地方偏,community概念淡的学校。大城市的氛围总是比较让我容易产生归属感和多巴胺,而这些因素其实是最利于自身向上爬的欲望萌生的。
我对于Boston这座城市是很憧憬的。有认识的朋友在那里读书,他们让我看见了一万公里外的红砖街道、结冰的湖,还有至今为止仍然会不时来一场的大雪。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我想看那样美的雪景。因为各不相同的理由排除掉一些学校后,我把目光投向Boston University (BU), 这座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学。社区氛围友好,校园活动多,就业前景好,生活便利,这些都是BU广为人知的优点。在我频繁关注他们的官网后,我发现了更多这个大社区吸引我的地方:鼓励学生经营校内事业,比预想中还要广阔的多元化,教职工和学生之间积极的链接,等等。BU充满活力的校园氛围让我相信,这里不仅能让我追逐学术梦想,更能让我感受到BU Terrier(梗犬,学校吉祥物)精神——勇敢、坚韧、充满活力——正是我希望在大学四年中培养的品质。

文书的极限重修
这是一件当时特别让我的申请老师们揪心的事情吧,哈哈。离截止上传日还剩大概一周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喜欢那个经过多次线上会议讨论出来的文书大纲。此时,在这个基础上由文书老师撰写的稿子已经改至距终版只差润色的境地了。
在那篇文章里呈现出的是一个成熟到让人难以挑出错处的申请人:她英语修得如同母语般行云流水,词汇搭配信手拈来,能够在运作社团时和带领以色列人的摩西共鸣,是发着光的共情者,变革者,领导者。但是这和我有出入吧?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写不出来复杂结构的长句。我对那个摩西的典故都一无所知。看见"Moses"时,我会先想到我那可爱的外方校长Chris而不是另一位传奇领袖 -- 毕竟Moses也是他的姓氏。总之,我花了一天时间好好考虑,明白心里这道坎过不去。我更想让未来的大学接纳那个不完美但真实的我。可申请季所有人都忙得焦头烂额,我没有理由揣着毁约的歉疚去请老师,叫她再因我的临时起意争分夺秒地创造一版新的。这也不人道。
随后我心里有个声音说:她很厉害,但是她写不出合你心意的样子。毕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了。
所以我决定自己写。
记得那一周我连上课都在悄悄敲字,寝室熄灯后和朋友讨论到深夜,睡了片刻后白天起来两眼发花地接着琢磨遣词造句。但我感到发自内心的愉悦。我的文书终稿包含了我全部想要展示的特质,编织进了我这三年热爱并为之努力的事,佐以我喜欢的一个趣味开头。尽管这篇浓缩至564词的文章在招生官的视线里只会存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可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对自己才最重要,它是我的“交代”。

其余情况:较稳定的校内GPA,不高不低的托福、光杆司令标化&竞赛
除了文书之外,我别的申请筹码几乎就走的“顺其自然”的路子。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申请规划和要求即:做自己喜欢且愿意投入的事情就好了。因为我认为假使逼自己关注不感兴趣的,用处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我的校内GPA始终保持在4以上。平时里我其实不算特别用功的学生,但是我在考前是比较疯狂的。一般期中期末这类考试的来临就代表着我每天熬夜温习到2、3点的时候到了。我一直以来习惯的模式就是爆发式学习,当截止日期逼近,所有借口无所遁形时,逼着脑细胞如岩浆一样倾巢而出 -- 火山喷发嘛。学习本身虽然不让我感兴趣,但“攻克学习”令我感觉干劲充足。试试“吓老师,同学,吓课本一跳”或者“不能被这种很傻的知识看扁了...”这种心理,还有不要说“我做不到”。总之,一是听课难以保持专注,二是做不到每天踏实稳定效率如神,所以我选择阶段性对自己狠一点。
回到申请。我的语言考试分数并不高,但途中努力了,考的几次分数也一直在进步,也就问心无愧了。我没有SAT/ACT成绩,竞赛记录更是空空如也。不过,我对我提交的活动列表还有文书是很喜欢且自豪的,它们完完全全属于我。
这种淡淡的自豪的确一直流淌至收到Offer的那天。当我有天早上起床看见微信里满屏的恭喜后,心里是一种意料之中,古怪又踏实的感觉,想的是:我就说我肯定中吧。
于是我的高中奋斗生涯就在这个没睡醒的清晨里大致落幕了。
 说来惭愧,打小学毕业后我几乎没有自发地去读完哪怕一本有帮助的书。除了一些文学课程规定要读的书籍之外,我从未对自己下定决心,总是处于和不同借口斡旋的境地。一会儿觉得课业重了,一会儿想着该陪家人了,明日复明日了这样几年。文书定稿后的某天,我突然意识到那564个单词像一根细绳,勉强捆住我贫瘠的阅读史——那些为应付作业快速翻完的书,那些借口“没时间”错过的思想。如果我连他人的文字都未曾真正聆听,又如何能在将来需要时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想要拾起那项似乎遥远了的、少时引以为豪的爱好。我开始看书,这成了我后来几个月中最主要的事情。没有拖延的借口,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人推着我去完成一个需要在周一被检查的阅读作业。
说来惭愧,打小学毕业后我几乎没有自发地去读完哪怕一本有帮助的书。除了一些文学课程规定要读的书籍之外,我从未对自己下定决心,总是处于和不同借口斡旋的境地。一会儿觉得课业重了,一会儿想着该陪家人了,明日复明日了这样几年。文书定稿后的某天,我突然意识到那564个单词像一根细绳,勉强捆住我贫瘠的阅读史——那些为应付作业快速翻完的书,那些借口“没时间”错过的思想。如果我连他人的文字都未曾真正聆听,又如何能在将来需要时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想要拾起那项似乎遥远了的、少时引以为豪的爱好。我开始看书,这成了我后来几个月中最主要的事情。没有拖延的借口,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人推着我去完成一个需要在周一被检查的阅读作业。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种如同与生俱来的赏析和阅读的天分再次回到我的世界里,我有些惋惜之前简直是残忍地浪费了可供读书的时间。
不过还不算晚,我这样想,心里又窃喜一阵。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有三个礼拜成年,还有半年不到就要去一个动不动就下漫天大雪的城市念大学。抱着罐子的少女雕像,她的身旁在个把月前盖起了新的学生宿舍,一旁的草坪上放置着学生们为猫们造的木头房子。也许深厚的情感可以将记忆无限修复直至清晰,每段时光里的校园角落都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里是承载我全部青春的地方,要形容如此磅礴和温柔的情感,我想只能用“爱”吧。我爱这里。
多幸运经历如此深刻、难得、快乐的一程。因此毕业前夕我怀着感激的心写下这些回忆,愿伴随我们的快乐能够细柔绵长。

文 |
排版 |
任同学
Nong